青年作家向莫言学什么
《收获》《当代》《十月》《花城》,号称是中国纯文学期刊的“四大名旦”。四种刊物上发表的文学作品,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当代中国文学创作的风向标,从这些作品可以清晰照见中国当代文学的面相。从本期起,羊城晚报推出“期刊观察”栏目,邀请几位新锐批评家追踪阅读四大文学期刊,追源溯流,探隐寻幽,为当代文学把脉。

□唐诗人
A、小说与故事的分界
莫言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五年没有新作,自然会遭受一些议论。比如最常听闻的一个,是说莫言丧失了创造力、再写不出好作品了,还有人甚至揣测莫言会停笔不再创作。直到2017年,他开始拿出一系列作品,分别在《收获》《花城》《十月》《人民文学》等刊物集中推出。其中,《十月》杂志将莫言短篇小说《等待摩西》以及另外三首诗歌放在了2018年第一期。莫言出新作,且是多年之后集中推出,自然是一件值得关注的文学大事。
莫言的文学创造力如何,值得探讨。在深入之前,可以给出我的观点,即莫言在《十月》2017年第一期发表的新作《等待摩西》,以及在其他杂志发表的《故乡人事》《天下太平》《诗人金希普》《表弟宁赛叶》等,整体上没有超越之前他自己的作品。莫言最擅长的是长篇小说,而这些新作很大部分都是短篇小说,就短篇小说来看,这些新作也没超越他早期的《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等。
自然,没有超越自己的经典作品,这并不是说新作就一无是处了,更不意味着莫言失去了文学创造力。毕竟,我们不能要求一个作家每次推出的新作都能超越自己之前的作品,这是不现实的。因此,这里说莫言这些新作没有超越他自己的经典作品,主要指他没再刻意去创造新的文体风格,不再是通过文体的独特和语言的迥异来吸引读者的眼球。可以说,莫言很大程度上回归了、或者说坚守了自己作为一个讲故事者的基本身份。莫言在诺奖的授奖词里强调自己就是个讲故事的人,这是大实话。小说家都是讲故事的人,只是有的人讲得好,有得人讲得差,更进一步说,是有的人讲成了小说、艺术品,有些人一辈子都只是故事编造者。从故事到小说,这之间并不是毫无间距的,而是充满学问。小说与故事的分界点难以说清,但却是我们评判好作家、好作品的根本所在。
B、写出好人的坏,也写出坏人的好
故事离小说艺术有多远,或者说一般的故事与好的小说之间的差异,最明显表现于通俗小说与伟大小说之间。通俗小说的故事都极好看,但伟大小说的故事不一定特别好看,即便是好看,也还有好看之外的让这小说真正杰出的因素。莫言说自己是说故事的人,但他的故事,没有一个可以算作通俗故事,比如不会有人认为《檀香刑》这种内容残酷以及《丰乳肥臀》这种题目看起来很是香艳的小说是通俗故事,它们反而是莫言最为重要的,在我看来也是艺术性突出、精神含量最为饱满的两部长篇巨著。这两部小说最明显地看出,莫言的讲故事不仅是叙事技巧上的智慧,更是思想精神上的杰出。在最新《等待摩西》里,作为短篇,它框架简单,却也延续了莫言在叙事和精神层面的可贵特征。
《等待摩西》的故事还是东北乡的人物故事,与《故乡人事》可以算为一系列,但这篇勾勒的人物生命更为完整。莫言以“我”的视角去讲述一个同乡、同学柳卫东一辈子的遭遇。柳卫东原名柳摩西,是其姓基督的爷爷取的。但柳卫东小时候参与运动,造了自己爷爷的“反”,也把自己的名改了。改革开放后,柳卫东出外做生意,没几年后,做生意再没回来,失踪了三十五年。最后,柳卫东又突然回到东北乡,是作为一个奇怪的基督徒回去的。要在一个简单的短篇里勾勒一个人的生命过程,肯定不会有太多的生活细节描写,也不可能侧重呈现现代文学以来流行的心理意识内容。莫言选择的还是比较通常的记叙,记叙“我”从各方面、各种人口中描述的柳卫东,记叙“我”自己与柳卫东几次接触时的日常对话,当然也少不了一些人物神情描写。回忆式地记叙,记叙听他人说与同柳卫东本人对话,这些看似普通的叙事方式,在莫言那里,使用得浑然入化。不但把柳卫东的生命过程表达清晰了,也将他身边的人的人性心理传达出来,最为微妙的还是,莫言所勾勒的这一切,每一帧都牵动着时代文化,都牵涉着我们的基本人性。莫言曾有创作论强调,写作就是写人,写完整的人,写出好人的坏面,也写出坏人的好面,《等待摩西》即是这方面的极好范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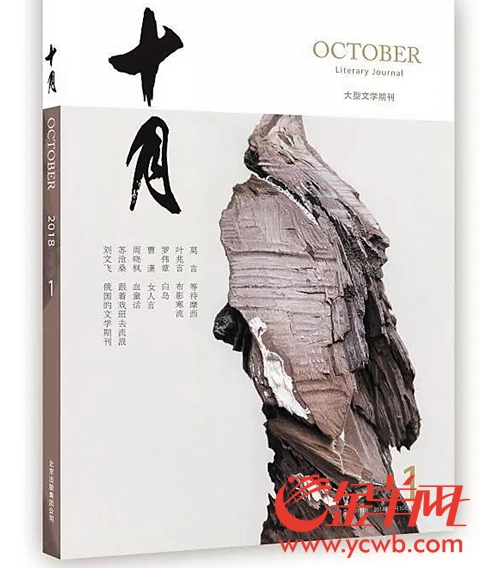
C、根本差距在于精神内核
《十月》这一期刊出的小说,有很多是青年作家作品。我们可以就此比较一番,看看青年作家可以向莫言学点什么。《女人言》《大幻想家》是这期《十月》“小说新干线”栏目的作品,作者曹潇,是个八零后作家。这两篇小说跟《等待摩西》有相近处,也是写人,也是对话多。但是,很明显,曹潇讲故事的能力远不如莫言。就结构上而言,莫言的技巧浑然得体,而曹潇《女人言》看似自然的组合方式里总有些刻意营造的人工痕迹。莫言用的“我”,和曹潇用的“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角色,前者是去言说他人,后者更多的是言说自己,即便第二篇《大幻想家》主要是为了讲述他人,也总是大幅度地扯上自己的感受之类。这可以说是小说的叙事目的不同,但内在隐藏着一种叙述智慧的高下。
小说家只讲述“我”个人的经历和内心情感的时候,格局必定有限,而虚构一个他者来帮助“我”自己发泄内心世界的秘密,这种叙述方式也更容易讨人嫌。反过来,小说家夹带着自己的视角去讲述他人的故事时,可以营造出更为真实的情境氛围,也更符合讲故事、听故事的心理逻辑。我们听故事时的基本心理期待,是听人讲述一个其他人的故事,而不是听一个人自己诉说自己的内心,后者天然地不那么受欢迎。这种差别,可以直接解释为什么读莫言的小说是愉悦的、通畅的,而读《女人言》则感到繁累、啰唆,需要耐着性子。
讲故事的能力,一个是结构,另一个是精神。曹潇与莫言的差距,不仅在于叙述结构、技巧层面,更为根本的,还是精神内核。曹潇的《女人言》《大幻想家》都格局有限,指涉的问题也特别简单,基本限定在情感遭遇导致人心闭锁、男女情感的复杂与纯粹。而且,对这些问题的思索,作者也并没有特别值得言说的思想基石。换而言之,这些故事跟我们的时代构成不了特别有意义的关联,它们是细碎的心情,可以讲述,却不是不得不的讲述。
讲故事的能力,是莫言身上最为可贵的财富。这个能力,不仅是叙述技术层面的智慧,更是精神思想层面的不俗与可贵。这也是当前青年作家最为致命的弱项,是青年作家们最需要向莫言学习之处。即便如本期刊出的蔡东的《照夜白》,在叙述的缜密度和人心的把握上,都做到了纤细与精准,有其特别难得的精神面向,但在宽阔度上,还是无以承受住莫言小说所容纳的历史与生命。在这个普遍推崇精细巧的时代,研习莫言小说的美学与思想魅力,接续文学史上伟大的精神传统,是青年作家急需完成的重要课程。


37afdb01-1f2d-462e-ab21-941dce8e8e55.jpg)
d29dce0e-f990-420a-ab47-6a48772edd07.png)
6fca286d-6d61-4650-9dfa-37e106477903.jpg)

2a2450fc-a57b-43b9-ad22-637fc1daee62.jpg)
dfa6990d-fcad-43a8-a87a-941536b72782.jpg)
c9ddb7e8-e194-486f-af39-4ac34cf5b5f9.jpg)
5f281fcd-3bf9-46ec-948a-bcdbc8e4ca1f.jpg)
4fa22fee-aaa0-4a4e-a38d-40c4b5d8b56d.jpg)
7b1fb3e1-a056-4f62-9815-905f32dfacab.jpg)
2cb16e35-f97f-48f4-a436-b373d40449f4.jpg)
031da51e-eab8-474b-9321-5ba3b890872b.jpg)

82a45120-0dc4-42bc-9b14-125dbbe37575.png)
7b599081-d40b-4b6d-b51c-3ee92afc15ce_watermark.png)
8827005e-1dad-42da-a468-9244601f9070.jpg)
3e46049e-8d9d-4256-8e3b-cb2bc77bf100.jpg)
304c0eeb-f100-4b2e-af7e-3699fe66aae5.png)
ffce7f5b-8b91-4d98-a5a8-84eb4f1a2c4f.jpg)
732b692d-4f2c-48d7-8342-e5a8c0e74056.jpg)
41c541b9-c350-4f50-b406-a674aac1d9f0.jpg)
b55b367f-e304-4623-8958-3920cd951bd6.png)
7fec6da1-497e-407a-ada6-202a35920845.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