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 梁宁 粤卫信(除署名外)
“六月谷子满,北寒鬼上床。十人九个疟,无人送药汤。”这是上世纪50年代广东的一首民谣,形容的是当时疟疾的猖獗。疟疾,这种寄生虫病在我国至少有3000多年历史。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据估算,广东每年约有200万—300万疟疾病人。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抗疟斗争,自2010年广东惠东县报告最后一例本地感染病例后,全省再无本地感染疟疾病例报告。日前,广东已顺利通过省级消除疟疾终审评估。
广东是如何做到消除疟疾的?4月26日“全国疟疾日”前夕,记者找到了数名广东抗疟专家,听他们讲述本土抗疟的“广东故事”。

调研
以自己为“饵” 几年努力终寻得“元凶”
今年85岁的黄祺林是原广东省卫生防疫站寄生虫病研究所所长,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直至退休,他一直致力于广东防疟抗疟工作。
“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医生是不会血检疟原虫的。尤其是在基层,检查手段匮乏,不看厚血膜。研究发现厚片和薄片(疟疾筛查手段)的检出率相差20%,而当时很多医院只检查薄片,也就是说,有两成疟疾病人可能会被漏诊。”黄祺林回忆说。为了更好地防控疟疾,上世纪50年代,广东在从化、丰顺等地建了6个疟疾防治站。黄祺林一毕业就在疟疾防治站工作,今年84岁的叶来添1957年中专毕业后也被分配到从化疟疾防治站。他们和同伴一起,承担着疟疾流行病学调查的任务。
说是调查研究,其实都是苦差事。黄祺林说,上世纪50年代初期,广东疟疾疫情大规模爆发,“我们就去疟疾流行区蹲点,一蹲就是五六个月,进行调查研究和送药”。
虽然都知道疟疾是由蚊虫传播,但当时并不能确定哪种蚊虫是罪魁祸首。为了搞清楚,黄祺林和同事们好几年都在和蚊子“打交道”,白天研究解剖蚊子,晚上去抓蚊子。蚊子可不好抓,他们以身体为“饵”,待蚊虫一停留在露出来的手臂、小腿等部位时,就立即用口把它们吸进小管子里去。
“蹲点的地方都是村民们的牛棚、猪栏、茅房等地,又脏又臭,因为那里蚊子最多,一蹲就是一个通宵,每15分钟抓一次蚊子。”黄祺林说。
在黄祺林和同事们的努力下,广东的疟疾传播媒介报告出炉,确认了中华按蚊是广东平原地区的传疟媒介,微小按蚊是山区和丘陵地区的主要传疟媒介,大劣按蚊是海南岛山林地区的主要传疟媒介,为此后的本地疟疾防控提供了科学依据。

防治
制度不断完善 疟疾疫情得到控制
除了做调查研究,黄祺林和同伴们还给老乡们送药。送药不是把药发给村民就完事,而是要“送药到手,看服到口”。“因为药太苦了,很多人会吐出来。所以,我们和当地医生们一起,送药给村民,还必须盯着他们吃下去。”一个疟疾病人要服药8天,每一次都得“盯着”。
黄祺林说,很多同伴在防疟过程中都感染了疟疾,“当时有过粗略统计,约10%的医生感染过疟疾”。
叶来添就是感染者之一。在防疟工作中,有一天他突然发烧不退,头晕乏力,验血发现感染了疟原虫,于是赶紧吃药治疗,幸好很快康复。“得了疟疾是很难受的,先冷后热再出大汗,热的时候很煎熬,冷的时候盖两床棉被都不行”。
血检发现疟原虫,如今看似简单的检查在当时却推进得不容易。叶来添回忆,1965年,首次在台山等地建立了7个疟疾血检站,对所有发烧病人都开展血检排查疟疾。“血检站相当于一个哨点医院,筛查出来的疟疾病人会立即得到专业治疗”。
随着血检站经验的成熟,广东逐步建立、完善了省、市、县(市、区)、乡镇四级医疗机构的“三热”病人疟疾血检、疟疾病例诊疗和管理、传疟媒介监测等制度,对及时发现、报告、处置可能存在的疟疾传染源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上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广东疟疾疫情渐渐得到控制,疟疾防治工作也从原来的“广撒网”转向了对“重点人群”。哪些是重点人群?叶来添说:建筑工地、高发病率的村庄、流动性大的砍伐民工等,工作方法依然是送药到手和杀虫剂滞留喷洒灭蚊等。
“革命”
疫情一度“抬头” 新防疟经验推向非洲
不过,上世纪80年代初期,疟疾发病一度有“抬头”趋势。黄祺林在《广东省1980—1987年疟疾流行状况》一文中写道:1980年-1987年,疟疾年平均发病率较解放初期下降了99.35%。然而,由于人口流动频繁,常常出现疟疾暴发点。其中,深圳疟疾疫情严峻。据记载,1983年—1985年,深圳相继出现输入继发疫点261个,占同期全省疫点总数的79.1%,波及20多万人口。
“当时疟引发疟疾暴发,流行原因主要是外地传染源输入和聚集,加上临时工地居住条件比较简陋、拥挤,防蚊灭蚊设施差,医疗卫生机构不健全,给疟疾的传播和扩散提供了良好条件。”黄祺林说。
1984年,深圳疟疾发病达到了建市以来的最高峰,报告病例7427例,年发病率高达1833.37人/10万。“当时深圳向全国公开招聘防疟专业人才,估计全国共有100多名专业人士迁移到深圳工作。”据黄祺林回忆,用“溴氰菊酯”浸泡蚊帐和强调睡眠挂帐措施的推广,让深圳疟疾疫情得到了控制。“溴氰菊酯浸泡蚊帐”是原广东省卫生防疫站寄生虫病研究所老副所长李祖资发明的。
叶来添当时也长期在深圳做疟疾防控工作,在他看来,使用溴氰菊酯浸泡蚊帐的防疟经验,“是抗疟工作的‘二次革命’,‘第一次革命’是1958年后的DDT(双氯苯基三氯乙烷)滞留喷洒灭蚊”。
事实也证明,使用溴氰菊酯处理蚊帐防制疟疾媒介的方法效果明显,这一方法后被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使用,并向非洲各国疟疾防治中推广。
消灭
推进联防联控 8年无本地感染病例报告
黄祺林和叶来添都认为,加强区域协作、推进联防联控是广东最终消除疟疾的重要举措。1990年,广东建立了“深东惠”灭疟联防区;同年,广东封开、怀集、连山县也与广西的邻县建立粤桂邻县联防。1992年,粤桂琼三省(区)疟疾联防建立,对流动人口疟疾开展联合管理。
“多地联防,多部门参与,信息互通,才能真正管理好流动人口疟疾和巩固抗疟成果,这样的经验同样适用于现在的各种传染病防控。”广东省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专家林荣幸说。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难抗疟,2010年,惠东县报告最后一例本地感染疟疾病例后,广东再无本地感染疟疾病例报告。“这是广东省疾病防控史上的又一伟大成就,凝聚了全省几代疟防人的艰苦奋斗历程。”广东省疾控中心副主任何剑峰说。
如今,广东防疟抗疟经验早已走向世界。广东本土科学家、广州中医药大学首席教授李国桥带领的广州中医药大学青蒿研究中心抗疟团队,从2007年到2017年,在东非岛国科摩罗摸索出一整套适应非洲当地的抗疟模式——“青蒿素复方快速清除传染源消除疟疾项目”,终于在这个疟疾肆虐的国家实现疟疾零死亡,疟疾发病率下降幅度达98%以上。如今,这一项目已在非洲国家马拉维、多哥、肯尼亚和南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推开。
广东省疾控中心副主任何剑峰指出,尽管广东实现了消除疟疾目标,但输入性疟疾病例引起的继发传播风险依然存在。2018年,全省报告输入性疟疾病例199例。
为了防止疟疾再传播,2016年,广东出台了《广东省消除疟疾工作方案(2016-2020年)》,该方案明确,广东将以口岸为单位,对境外疟疾流行区入境的、不明原因发热病人全部进行疟原虫血检或RDT筛查。此外,还将在口岸强化疟疾防治咨询服务,加强检验检疫机构与疾控机构合作,减少疟疾病例输入。
ea9e225c-63e7-4aee-930f-0bcb687fe288.jpg)

1955fd34-2ebb-4c6a-a24d-46ad734d9426.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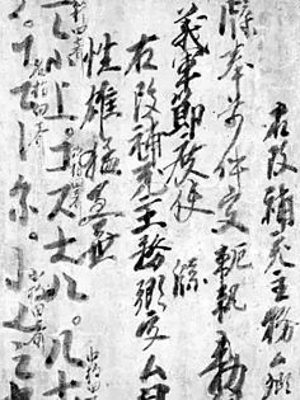
2a40ae8e-2adb-435b-8478-4a7e269507dc.jpg)
14248d39-3255-4c89-9352-35e03ab51dcfa5ee6385-a43e-4ba5-a896-a66eee479a52_zsize.jpeg)
4dfbb190-a451-4edb-a258-0b178f8bb0ec1d40280c-1203-49dd-9769-9e967ffffbc4_zsize.jpeg)
5a443ad0-deab-484c-9f64-6e7ee95c547776a51e41-3417-4f37-8dc0-f9e8cb62d761_zsize.jpeg)
3a1c6201-93d6-40cd-ba3d-b479c404b78b93cd0bf9-2a7e-48b0-b163-bd0abd7c0bc3_zsize.jpeg)
4210ad60-0468-4979-9bc4-292ff6a0296761785182-f045-4b36-892c-0dccfe20fa5c_zsize.jpeg)
84603f73-89dc-44ca-bd24-f047812136f1ba84abdd-530f-43fd-a613-dba26a3fa50b_zsize.jpeg)
22217174-5445-451f-8e09-83aac25229a14205f5b0-bc25-4905-877a-f84cdc105e10_zsize.jpeg)
0039877d-ca58-4757-baef-fcb83b0dcde4.jpeg)

b9676953-ad7a-4fce-91f0-ea1093309767.png)
81704305-e1fb-4bc9-b8dd-c21dc189b626.png)
0d279b68-b2ca-4bdc-85e9-52995f0925c9.png)
f0a51d21-dd54-41a9-ad9b-ef18162ce1296bb03cd6-76e1-4d45-9a49-e70594a27547.jpg)
5fd440c7-891d-4392-80fb-3c020ad10b78.jpg)
eb127f8c-bf8c-4c41-a37d-c45d6d8668c3.jpg)
c8634918-89ee-4828-a097-d8549791dc68.jpg)
374fc89b-2f1b-4b08-ad30-8229cee380a6.jpg)
2f62fc80-062b-400c-96d2-7b7522da0c92.jpg)
102aea11-d9d5-4ec5-a7ce-6d82bb90f0d00222cd95-2ea9-4883-9e01-001023ca057a.png)
